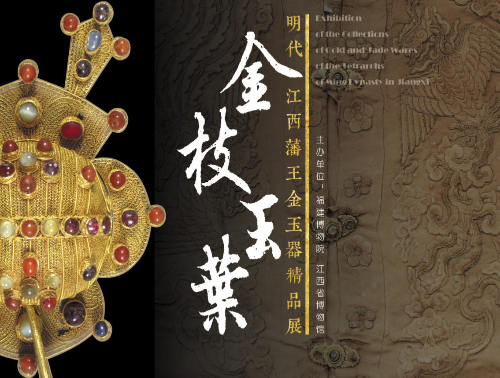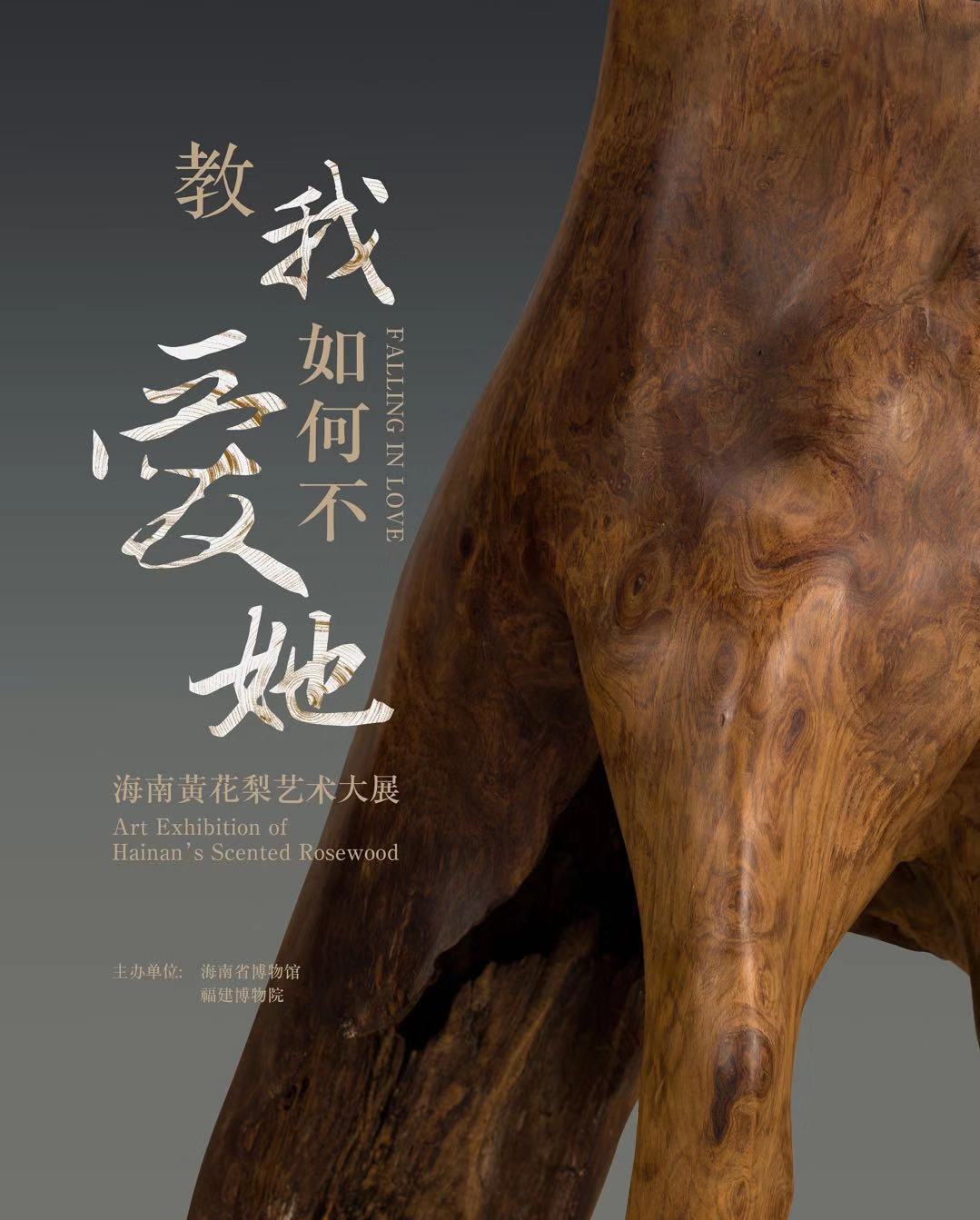“我與中國文物報”征文 | 從“零”到“一”
| 2020-08-20 16:24:47??來源: 責任編輯:陳靜 我來說兩句 |
分享到:
|
我是一名即將入校的碩士生,也是一個考古人,即便有過茫然,想過放棄,但我更欣慰自己留了下來。我滿含柔意地看待昨日所做的決定,也期待明天時光賦予的溫情,而此刻,我心篤定。 緣 起 2018年8月,帶著憧憬,我有幸前往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遺址參加本科田野考古實習。基于發(fā)掘人數的需要,探方多而集中,又因遺址堆積較厚,產土量自然不小。日常向外輸土通常依靠人力獨輪車,長此以往,車碾人踏下的發(fā)掘區(qū)地表早已粉土一片。加之當時發(fā)掘的區(qū)域四周林木稀少,整個工地無須勁風來襲,大有西北刮沙塵暴的架勢,曾幾度影響發(fā)掘。 時值帶隊老師交接,后來者自是驚了這陣勢,下工路上我與其閑敘,言及考古工地的粉塵問題,不承想他提議從考古與環(huán)保的角度切入,可做探索。由此便有了首篇稚文——《淺談考古工地的環(huán)境保護——以我國北方考古工地為例》,我左思右想,又經多次修改,最終惶恐地投給了《中國文物報》。 意 外 2018年12月底的一個夜晚,正當我寫罷探方日記,突然得知文章發(fā)表的消息,身體剎那間出現麻木與魔怔,清醒過來又怕惹人注意,故暗藏喜悅,獨自去了屋頂。我快速撥通了摯友的電話,在夜空中揮舞著拳頭,擲地有聲地告訴他,“我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我要考研,要干考古,即便這條路荊棘遍布,我也要走上一遭!”那沒有預期的驚喜,激揚歡悅的心情,我至今仍記得當時的諸多細節(jié),記得那個刻骨入心的日期:2018年12月14日。 語無倫次后我掛了電話,伸開雙臂,盡可能延展自己的胸膛,企圖吸納那刻的每一縷空氣,仿佛擁抱世界的同時,世界也在擁抱我。那個夜晚沒有燈,但我的周圍卻盡是光明。 饋 贈 再次回到學校,已是備戰(zhàn)考研期,也來不及彷徨猶豫,覺得自己既然可以寫,就當堅定地寫下去,結合自身具備臨摹繪畫的技巧,喜歡安靜做事的個性,更將從事考古認定為職業(yè)與理想的結合體。而《中國文物報》給予的認可,也讓我在這條路上收獲了不少支持與贊許,甚至于飄飄然前進。 但直到考研成績公布時,夢碎的聲音襲來:比往年國家線還低一分。我不由得沉默,仿佛立足的地方就是萬丈深淵,但又不得不口頭輕松地面對結果……正當心灰意冷之際,傳來國家決定擴招研究生的消息,2020年國家線下降一分,這一分讓我起死回生,繼而我憑借面試的出色發(fā)揮和曾在《中國文物報》發(fā)文的優(yōu)勢得償所愿。 師父曾說:“跌過摔過,才是男兒”。誠然,抵達彼岸的路途必然坎坷,在選擇考古的艱難經歷中,有巧合、有幸運,但更難能可貴的是我遇到了你們。 回 首 2020年7月,我本科畢業(yè),雖然許多記憶匯聚心頭,但過往經歷中若論及難忘,卻唯此不多的幾例,我也至今仍小心翼翼地保留著《中國文物報》寄贈的兩份樣報。雖然相比于報社35年的發(fā)展歷史,一篇文章不過是滄海一粟,但于我而言,這份小成功不只是一個新的起點,更因它改寫了我的命運。更何況我熱愛考古,也堅信今后還會有所開拓。 我永遠感激那次沖動,又或是不自量力,它讓我擺脫的不單是由迷茫產生的墮落和不自信,更是接受自己,正視自己決意追求的職業(yè)與理想。我也十分感激那個秋冬與《中國文物報》的相遇,正由此,才讓一位懵懂學子步入考古研究的大門,不至于荒廢此生。 回首追尋考古的這幾年,光陰仿若一個坐標軸,旁人的指點,自己的求索就如同從“零”向“一”的無限接近,而真正撬動內心的還是在《中國文物報》發(fā)文的成功,它是真正到達“一”的象征,給了我莫大的勇氣和力量,讓我不負韶華,不失夢想,從容邁向人生的正無窮。 求學之路,波折起伏,所幸終究守住了夢想,其間深受《中國文物報》影響,愈久愈感其恩澤,由此撰文抒情致謝,亦是祝賀《中國文物報》創(chuàng)刊35周年。(甘創(chuàng)業(yè)) |
相關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