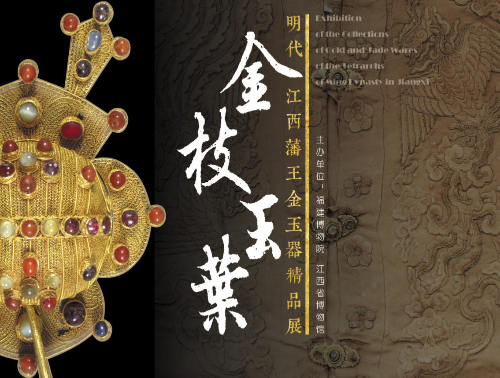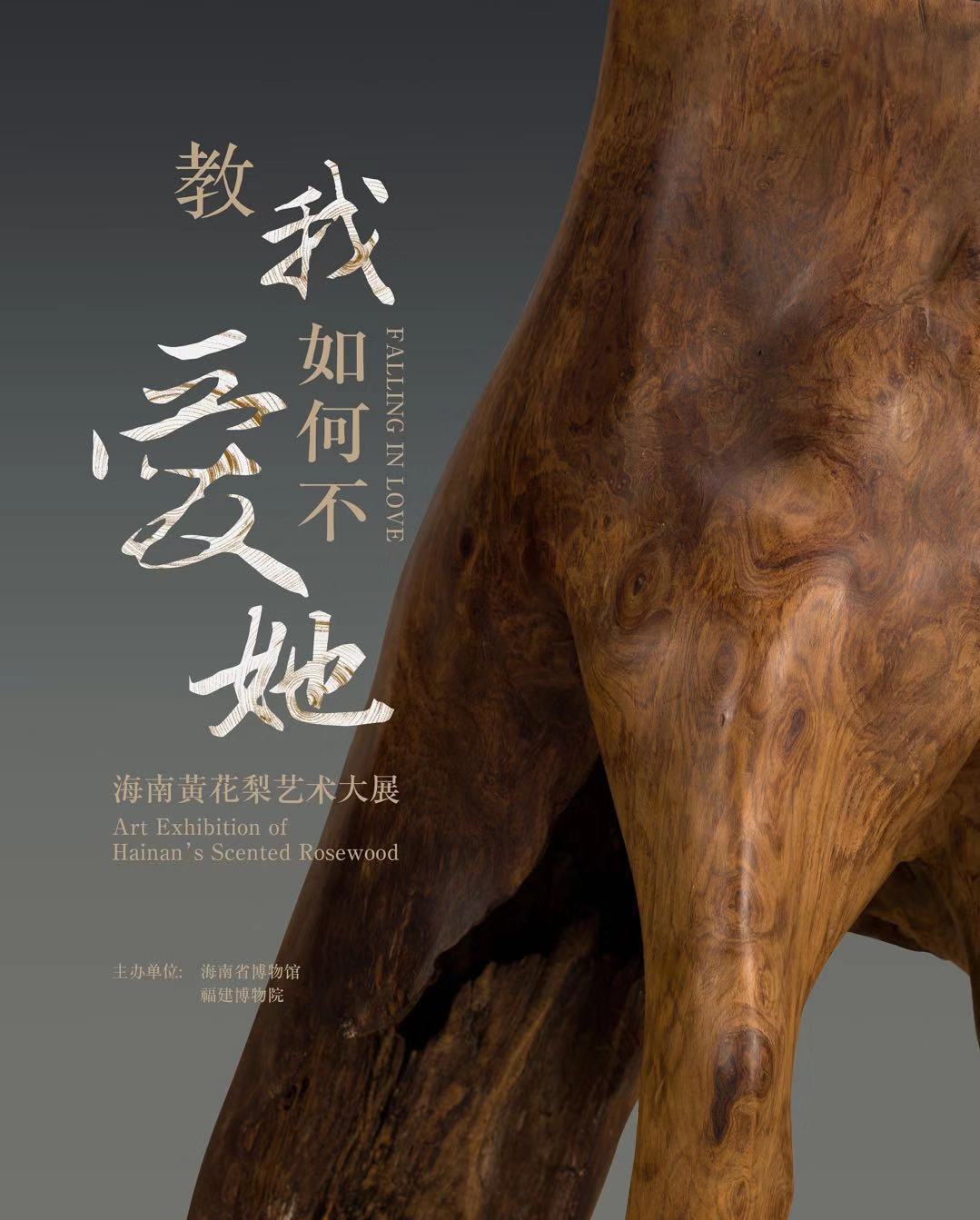“我與中國文物報(bào)”征文 | 讀者·作者·編者 過去·現(xiàn)在·未來——文物報(bào)于我猶如一座通往很多目的地的橋梁
| 2020-08-10 17:43:36??來源:國家文物局 責(zé)任編輯:陳靜 我來說兩句 |
分享到:
|
又見“我與中國文物報(bào)”征文。已經(jīng)記不清這是第幾次了,每隔幾年,報(bào)社都要搞一次同題征文,每次也都會(huì)有不同的人與文物報(bào)結(jié)成新的屬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關(guān)系,總會(huì)有一些難忘的內(nèi)容值得分享。2017年離開中國文物報(bào)社后,使我也有了回頭看的機(jī)會(huì),可以在一個(gè)總結(jié)性的角度反思我與這張報(bào)紙,以及報(bào)紙與時(shí)代的關(guān)系。 于是,悵然命筆。 報(bào)紙是媒體,“我與中國文物報(bào)”關(guān)系,其實(shí)也無外乎就是編者、作者和讀者的相互關(guān)系。就我自己來說,則一身兼過三者,其中有幾項(xiàng),于人于己,也可能都稱得上是難破的紀(jì)錄了。 我是報(bào)紙最早的讀者之一。1985年報(bào)紙剛創(chuàng)刊,我就開始了讀者的生涯。當(dāng)時(shí)正在大學(xué)最后的兩年,作為考古專業(yè)的學(xué)生,已經(jīng)到了專業(yè)思想初步確立、時(shí)間安排較為從容的階段,因此,每到圖書館閱覽室的事項(xiàng)之一,就是粗粗瀏覽一下最新的報(bào)刊,《文物報(bào)》當(dāng)然漸漸進(jìn)入了關(guān)注的視野。當(dāng)時(shí)文博考古方面的資料不算多,《文物報(bào)》有自己的特色,內(nèi)容豐富,短平快,尤其是報(bào)道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最受同行們重視。看報(bào)看出了興致,1987年大學(xué)畢業(yè)的那個(gè)暑假回家在鄭州換乘火車時(shí),我突發(fā)奇想摸去報(bào)紙編輯部拜訪,想一窺報(bào)紙的幕后究竟。記得主編武志遠(yuǎn)和編輯冷濤接見了我,聊了什么早已忘記,但擁擠的辦公室、凌亂的書桌、堆積如山的稿件等,則留下不滅的印象。 不久,我到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2003年并入中國國家博物館)工作,接著,《文物報(bào)》也打算遷京并更名為《中國文物報(bào)》,他們兩位常常到京接洽有關(guān)事宜,且多住在離我的宿舍不遠(yuǎn)的歷博東門外招待所。招待所位于天安門廣場附近,不僅交通便利,便宜,而且可以在博物館食堂搭伙,到包括文物局的各相關(guān)單位辦事也很方便。一來二往,大家竟然變成熟人,我也斗膽開始給《中國文物報(bào)》投稿。自1988年開始,幾篇介紹過程主義、后過程主義考古學(xué)的短文就相繼在《中國文物報(bào)》亮相。那時(shí)歷博館長俞偉超先生也常常給報(bào)紙撰稿。他寫出稿子后,會(huì)先讓館里的年輕人看看,定稿后則直接差我們送到報(bào)社初到北京時(shí)租用的交道口中學(xué)教室里的編輯部去,以繞開郵件的繁瑣和耽擱。 未曾想到編輯部后來也成了我的辦公室,成為我人生的錨地。2000年李文儒先生由國家文物局博物館司司長轉(zhuǎn)任報(bào)社社長,臨行前邀我加盟,于是,我從機(jī)關(guān)的辦事員轉(zhuǎn)身為報(bào)社的編輯。那時(shí)候報(bào)社已經(jīng)大有發(fā)展,并遷到了雍和宮附近的柏林寺。這里是一個(gè)文物保護(hù)單位,寺廟大殿高敞的空間被架出二層,再東西相對(duì)分隔成多間,一間就是一個(gè)部門的辦公室。編輯記者主要在二樓。發(fā)稿或者校樣時(shí),編輯們?cè)诟魑葜g來來回回不停地串門,懸空的木地板和木架子樓梯被踩得嘎吱嘎吱作響。有時(shí)候加班到晚上,空曠的寺院中,寂靜的夜晚里,這樣的腳步聲回蕩在漆黑且年代久遠(yuǎn)的樓道里,聽起來別有一番滋味。 高原街的文博大廈雖然也是一個(gè)報(bào)社的過渡地(2002~2006),但采編工作在這里首次實(shí)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在柏林寺時(shí)編輯部就已經(jīng)告別了鉛與火,開始采用激光照排印制,但編輯們還完全是手工作業(yè),臨離開之前才為每個(gè)部門配備了一臺(tái)電腦和打印機(jī),主要是接受個(gè)別作者的電子郵件投稿和打字。有一兩臺(tái)筆記本電腦,則是首席記者才能借用的。搬往文博大廈時(shí),入住之前每個(gè)座位就都配備了能上網(wǎng)的電腦,并全部采用當(dāng)時(shí)國內(nèi)首屈一指的品牌。剛剛起步不久的中國文物信息網(wǎng)也和報(bào)紙大致上同步更新了。 報(bào)社的小街橋社址,可能是我此生坐過的最長的辦公位了。2006年至2017年,我10年中沒有換過位置和桌子,在白花花的日光燈下送走了數(shù)千個(gè)日月晨昏,看稿也看得我提前有些老眼昏花。北小街2號(hào)樓二層朝北的大落地窗外正對(duì)著北京車水馬龍的北二環(huán),雖然吵了點(diǎn),但車聲風(fēng)聲不停地咆哮,每每加班到華燈初上時(shí),窗外各種霓虹閃爍,大都市的繁華與文物的古舊以及文字的沉靜在心底形成巨大的反差。隨著文博事業(yè)的發(fā)展,國際博物館日和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日的紅火,報(bào)紙編輯部開創(chuàng)的幾種節(jié)日特刊漸成模式,要短時(shí)間突擊采編制作超出日常每期報(bào)紙數(shù)倍的版面和專題內(nèi)容。為此,臨近出報(bào)時(shí)整個(gè)報(bào)紙編輯部常常要通宵達(dá)旦地奮戰(zhàn),有時(shí)候幾個(gè)人突擊完最后的工序后,繁忙的都市公交早已經(jīng)停歇了,大家只好就睡在辦公室或者坐等天亮。第二天一早自己首先看到工廠送來的即將發(fā)往讀者手中的帶著濃重墨香的報(bào)紙,卻并未如釋重負(fù),反倒是心情忐忑,害怕看到忙碌中不經(jīng)意犯下什么編校上的錯(cuò)誤,修訂重印的事情也不是沒有發(fā)生過。 我自2000年10月入職中國文物報(bào)社,到2017年5月調(diào)離,在報(bào)社供職了17年,絕對(duì)年頭不算太長,但報(bào)社肯定已經(jīng)是我此生服務(wù)時(shí)間最長的單位了。之前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原中國歷史博物館)10年,國家文物局3年,現(xiàn)在華發(fā)早生,行將退休,服務(wù)新單位的時(shí)間肯定不會(huì)再超過報(bào)社了。唉,人生苦短,此之謂也。 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是報(bào)紙的黃金年代。飛速發(fā)展的社會(huì),蓬勃的各行各業(yè),主要信息資訊都要依靠報(bào)紙這種新聞紙來傳遞,河南的文博工作者獨(dú)具慧眼,適時(shí)創(chuàng)辦了《文物報(bào)》,填補(bǔ)了行業(yè)空白,發(fā)揮了巨大作用。進(jìn)入新世紀(jì),報(bào)紙?jiān)诤突ヂ?lián)網(wǎng)等新媒體的競爭中因高成本、低效率而漸漸敗下陣來。報(bào)社的主要工作是編報(bào),俗話說的為人做嫁衣,不過我們覺得這人可都不是一般人,至少都是些舞文弄墨的文人,甚至有很多文博大家和領(lǐng)導(dǎo)。我常常對(duì)同事們說,不管是誰的稿子,有問題都要放手改。其實(shí)我們的工作也不僅僅是編稿,也包括采和寫。對(duì)于有些人,后者更重要。我自己確實(shí)有讀者、作者、編者、記者一身數(shù)任的感覺。 我常常自問,17年的媒體工作經(jīng)歷給我?guī)砹耸裁矗扛`以為最重要的是文體。寫什么、怎么寫從來都是個(gè)大問題。報(bào)紙文章不同于學(xué)術(shù)文章和著作,也不同于機(jī)關(guān)里起草報(bào)告、講話與公文等,短則數(shù)百字,長到數(shù)千字甚至一兩個(gè)版面,要把一件事情、一個(gè)觀點(diǎn)說清楚,讓專業(yè)人士不挑剔,讓領(lǐng)導(dǎo)干部和一般同行喜歡看,甚至是跨行業(yè)乃至社會(huì)上的普通讀者也看得懂,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要命的是,很多稿件需要立馬完成上版,不給你多少時(shí)間準(zhǔn)備和醞釀、潤色。這需要一些習(xí)慣、規(guī)則、文風(fēng)和文體方面的支撐,才能做到。 20世紀(jì)后半葉,各學(xué)科和各行業(yè)都發(fā)生過語言學(xué)或者信息化轉(zhuǎn)向,背后的推力是信息革命和社群重組,人們無論做什么,都需要表達(dá)、溝通,包括在社會(huì)中亮相,因此,媒體不僅快速行業(yè)化、產(chǎn)業(yè)化,而且需要和都市化的社會(huì)生態(tài)緊密結(jié)合,時(shí)時(shí)調(diào)整自身與公眾的關(guān)系。現(xiàn)代大都市已經(jīng)不同于傳統(tǒng)的城鄉(xiāng),不再是金字塔式的聚落結(jié)構(gòu),各種交叉的網(wǎng)絡(luò),各種要素、因素的發(fā)散式結(jié)合與重新聚合,滋生出很多新的人與信息的業(yè)態(tài)、生態(tài)。《中國文物報(bào)》不僅具有一般媒體的所有特點(diǎn),也是過去通往現(xiàn)在的一條信息的管道。相對(duì)于業(yè)內(nèi)較多的期刊和單位網(wǎng)站,《中國文物報(bào)》及其相關(guān)的網(wǎng)絡(luò)媒體可能更具交叉性也更接地氣,和一線的文博工作者以及社會(huì)各界具有更廣泛、深刻的聯(lián)系。報(bào)社周圍聚攏了一大批作者和讀者,對(duì)自身的生存和行業(yè)的發(fā)展都發(fā)揮了相當(dāng)積極的作用。盡管信息和媒介形式在不斷演變,但文博考古一類的信息內(nèi)容與社會(huì)作用卻越來越重要,我們見證了行業(yè)工作從社會(huì)冷門到公眾關(guān)注的急劇轉(zhuǎn)變以及遺產(chǎn)意識(shí)普遍覺醒的中華文化復(fù)興時(shí)代的到來。我的媒體工作經(jīng)歷也使我獲得了鮮活的媒體方面的體驗(yàn),這是知與行方面的直接錘煉。除了報(bào)紙,我們也嘗試著其他媒體形式的建設(shè)與探索,見證了報(bào)社網(wǎng)絡(luò)化、信息移動(dòng)化的進(jìn)步過程,體會(huì)到公眾對(duì)文物和文化遺產(chǎn)的摯愛之情,以及一個(gè)公共性和公益性很強(qiáng)的行業(yè)中科普與架橋工作的極端重要作用,還有博物館在行業(yè)中媒體性的特殊地位,乃至整個(gè)社會(huì)生產(chǎn)與生活的博物館化、遺產(chǎn)化與媒介化趨勢。這是一個(gè)偉大時(shí)代,已逝的歷史、文化乃至文明,借助科技與社會(huì)的進(jìn)步,重新回到現(xiàn)代人的視野、經(jīng)驗(yàn)與認(rèn)識(shí)之中,人類從以字為媒,快速進(jìn)入讀圖時(shí)代、全媒體時(shí)代,乃至直接以物為媒、以歷史遺產(chǎn)為發(fā)展資源的歷史性回歸,在信息與權(quán)力的格局中,文物和文化遺產(chǎn)的地位日益凸顯,讓文物活起來,讓文物保護(hù)與利用融入現(xiàn)代人的生活,全面重建文物與人的關(guān)系,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的兼容性發(fā)展,開始呈現(xiàn)出真正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文物報(bào)》的經(jīng)歷,猶如站在讀者與作者以及過去與未來的歷史交匯點(diǎn)上。 限于行業(yè)規(guī)模等原因,《中國文物報(bào)》的發(fā)行量一直不大,但覆蓋面和影響力還是很強(qiáng)的,口碑也不錯(cuò)。 總之,我在《中國文物報(bào)》的17年,可以稱得上是青春無悔。 (曹兵武) >>>征文選登 “我與中國文物報(bào)”征文 | 我做研究的好幫手和好推手 【點(diǎn)擊了解征文活動(dòng)詳情】
|
相關(guān)閱讀:
- 習(xí)近平:扎實(shí)做好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系統(tǒng)性保護(hù) 推動(dòng)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 推動(dòng)博物館高質(zhì)量發(fā)展 服務(wù)文化強(qiáng)國建設(shè)——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huì)文物司有關(guān)負(fù)責(zé)人就修訂《博物館運(yùn)行評(píng)估辦法》等文件答記者問
- 2萬余件(頁)731部隊(duì)暴行新罪證首次展出
- “數(shù)字敦煌·開放素材庫”上線 6500余份檔案開放下載
- 福建省首屆“福”文化論壇舉行
- 中國博物館協(xié)會(huì)科研課題資助計(jì)劃項(xiàng)目申報(bào)工作啟動(dòng)
- 《紅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第一季展播(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