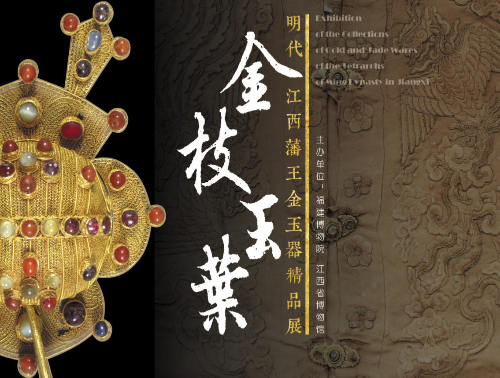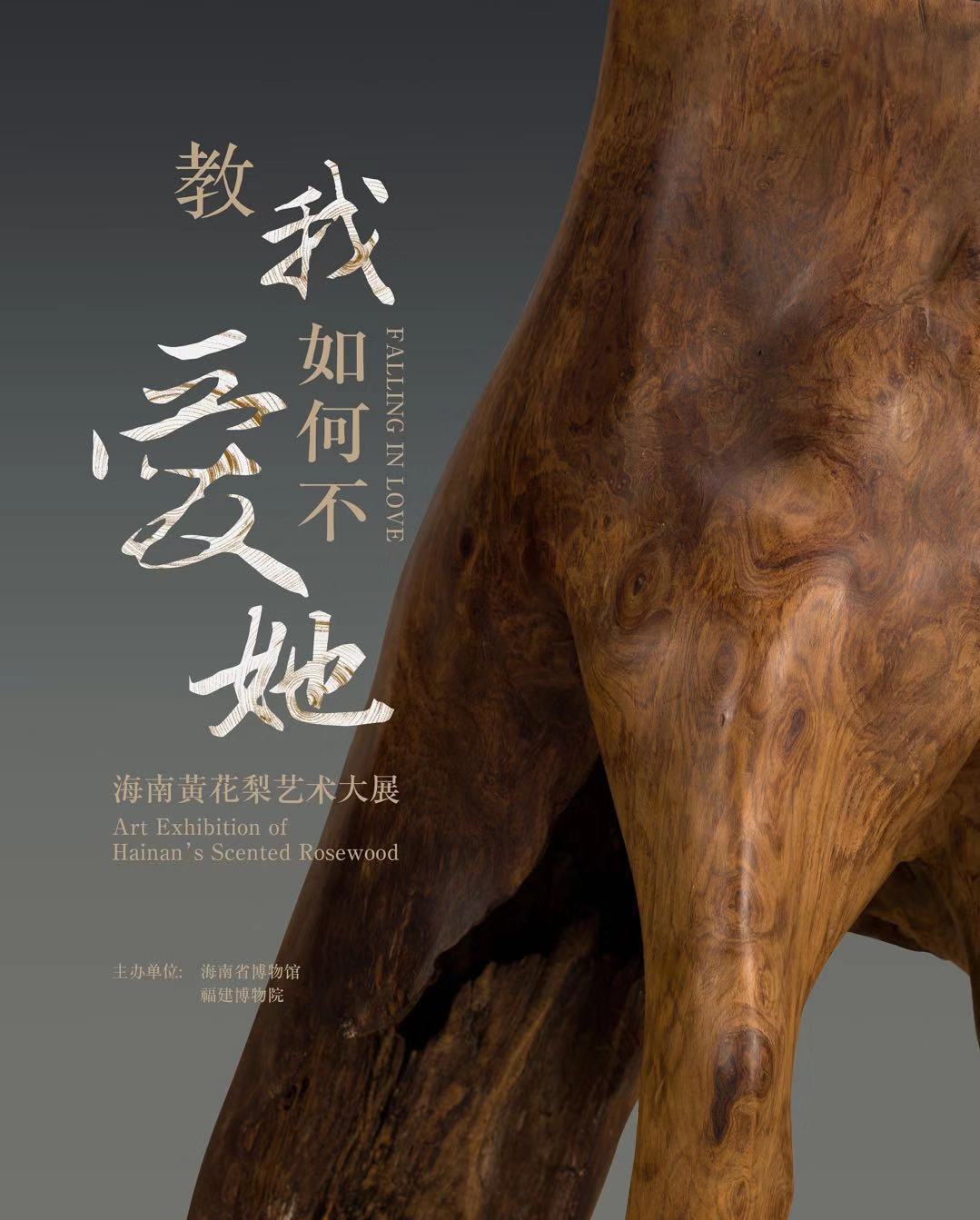基層文博人|黃利平:嚴謹務實 一步一個腳印探索新發現
| 2020-07-29 15:35:22??來源: 責任編輯:陳靜 我來說兩句 |
分享到:
|
黃利平,1956年出生,西安人。1986年,他從陜西師范大學研究生畢業進入陜西歷史博物館籌建處,從此與文博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2002年,黃利平調入廣州市番禺區虎門炮臺管理所擔任所長,2016年從廣州市南沙區虎門炮臺管理所(文物管理所)所長崗位退休。對待自己熱愛的文博事業,黃利平這30年來一直不斷挑戰自己,力求創新,發現未知。
黃利平準備出海。他負責管理島上的三個炮臺,坐船出海是日常工作。 結緣陜歷博 建功在南粵 1986年,黃利平進入當時還是一片麥地的陜西歷史博物館籌建處。當時籌建處只有正式員工20多人,處里的陳列準備科是博物館唯一的業務部門,黃利平作為負責人之一,在陜歷博長達8年的籌建過程中,從編寫大綱、征調文物、制定展覽到保管設備等工作無一不全程參與。開館前他和同事們忙于布展,大約半個多月都以館為家,吃住在展廳。特別是開館的前一天晚上一直工作到凌晨4點,稍微休息下就立即精神抖擻地參加了陜歷博的開館儀式。黃利平說:“一晃30多年過去了,現在回想起陜歷博開館前那段如火如荼的歲月,還歷歷在目。” 為了拓展工作領域,學習新知識,黃利平先從陜西到了廣東,再從廣州市番禺博物館到了番禺區虎門炮臺管理所,一邊感受了南粵工作的艱辛,一邊也收獲了挑戰成功的喜悅。 2002年,黃利平開始擔任廣州市番禺區虎門炮臺管理所所長,將文物調查的視野從關注陸地,轉移到海洋中的島礁上。南沙區200多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積,包含直轄島、礁有六七個。為了對這些海洋文物有清楚的了解,黃利平和同事們曾雇了一艘沖鋒艇前往珠江口外的舢板洲小礁石上實地查訪。沖鋒艇在風浪中行進了大約半個小時到了最遠的舢板洲燈塔,當地人稱“白塔”的腳下。黃利平和同事們研究后發現,這座“白塔”為法式建筑,建成時間已有百年,也正是因為這次海洋文物的探索,改變了沿海古港名城廣州,在文物圖錄中沒有自己燈塔的尷尬歷史。2015年,這座燈塔順利入選廣東省第八批文物保護單位名錄。 這次重大發現激勵著黃利平和同事們繼續海上文物普查。他們登上了只在資料中看到過的大虎島,進行實地普查。大虎島上的炮臺是虎門炮臺之一,黃利平和同事們在島上找到了清代嘉慶年間始建的大虎炮臺遺址,通過殘余的地基和石塊,確定了炮臺方位,他們也成為有記錄的、第一批登島進行實地普查的文博工作者。 黃利平來到廣州以后,閑暇時還很喜歡去看有特色的廣府傳統建筑,他對傳統建筑的祠堂、神廟的興趣越來越濃厚。2008年,他和文物普查隊在南沙區黃閣鎮東里村發現了一座很古老的建筑,卻沒看到常見的牌匾。當地鄉民告訴普查隊員,這座老建筑叫“輔黨麥公祠”,已經記不清建筑年代了。黃利平和同事們走進院子,抬頭就看見頭門上方一幅長約5米、高約1米的巨型壁畫,上面落款是“道光二十六年”。50多歲的黃利平毫不猶豫地爬上五六米的長梯,仔細察看了壁畫和兩旁略顯斑駁卻工藝精美的磚雕,認定這是一幅未經后世涂改的清代壁畫原作。壁畫在白灰底上用單一的墨色描繪了在云霧間的飛龍,具有國畫般的意境,是色彩艷麗的廣府壁畫中唯一的“水墨畫”題材,廣府人稱之為“水墨龍”。壁畫畫的是在烏云密布的天空中若隱若現的一條怒氣沖沖的老龍正在教訓一條誠惶誠恐的小龍。壁畫采用了宣紙畫“留白”的手法來展現天空的浩渺無垠,用墨色的濃淡塑造出了云海翻涌和見首不見尾的神龍。黃利平和同事們還對殘存著金漆粉末和精美雕刻的木梁架屋頂進行了逐一核驗,認定這座老建筑建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距今已有170多年。當年這幅“廣州最原始壁畫”的發現以及其中蘊含的豐富文化元素,引發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潛心虎門炮臺研究 長期以來,業內對虎門炮臺,包括對廣東沿海炮臺的相關研究都很少,炮臺及海防設施的有關研究更是近乎一片空白。黃利平擔任虎門炮臺管理所所長后,便開始潛心研究虎門炮臺,為了研究炮臺形制,他幾乎跑遍了廣東沿海現存的所有炮臺遺址。他反復比較各炮臺形制,找出其中共同點及差異之處,比如清代初期炮臺都是城堡式炮臺,大炮架在城堡的墻頭上;清代中期是炮洞式或稱垛墻炮口形式,大炮是架設在炮臺墻下邊的炮洞里;清代晚期是鋼筋混凝土的西式炮臺,與以前的炮臺完全不同……黃利平的這些研究不但提升了對原有炮臺的科學認識,還對新發現炮臺的判定有所助益。2003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學城穗石村發現一處大型炮臺,當時被認為是清初炮臺。但黃利平分析,如將大學城穗石村炮臺遺址形制,放在整個廣東省清代炮臺系列中就不難看出,它屬于典型的中期炮臺形制,通過現存的15個炮臺垛墻顯示它是一個炮洞式炮臺。黃利平說:“清代海防江防炮臺分期十分重要,如沒有分期理論,則無法判斷這類新出土炮臺的準確時代。”穗石村炮臺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所建的觀點,于2013年被發掘單位采納。 黃利平研究炮臺,對任何有效線索都不放過。在整理炮臺照片資料時,他的目光被一張80年前拍攝的照片深深吸引,對于虎門炮臺現存狀況了如指掌的黃利平一下子興奮起來,這張照片是1938年由日軍在虎門炮臺拍攝,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炮臺、大炮及附屬設備的情形,但遺憾的是照片中沒有注明具體拍攝地點,無法與現存炮臺實體進行對照。為了查證這張照片的確切地點,黃利平決定比對照片實地考察,幾經查證他認定照片是在上下橫檔島上拍的。上下橫檔島共有約20個炮臺,黃利平首先想到的是上橫檔島前山的3號炮臺,因為這個炮臺的大小同照片上的比較接近,照片里的珠江江景和武山山體至今也沒有太大變化。可當他興沖沖地坐快艇登上島時,卻發現從這里看過去,武山斷成了兩段,島上很多地方景物也與照片不符。黃利平只好又坐快艇去下橫檔島,當快艇在珠江上高速向南面的下橫檔島行進時,他不經意地回頭看了一眼武山,意外發現隨著快艇向南行進,武山的斷口竟然漸漸看不出來與照片一模一樣了。當他站到下橫檔島8號炮臺邊時真是又驚又喜,看到了與照片中一樣的山和水以及相同的炮臺、階梯和彈龕等建筑,這張照片當年的拍攝地點終于被確認了,為炮臺研究提供了準確的史料。 堅持科學嚴謹的專業精神 黃利平從事文博工作30年,其中20年在基層文博單位,他說:“不重視基層文博科研工作的觀念是極其錯誤的,基層文博工作更需要以科學嚴謹的專業精神來對待。因為在第一線,基層工作者往往就是決策者,稍有不慎就會造成工作上的損失,而且這種損失可能會因為認識不夠長期得不到糾正。”黃利平在海上發現百年燈塔后,撰寫了文章《廣州百年燈塔依然在崗》,燈塔受到相關部門重視并列入廣東省第八批文物保護單位名錄。在他發現道光年間廣府壁畫后,受有關部門委托主持編輯出版了《廣州傳統建筑壁畫選錄》等書籍,并發表科研文章,廣泛傳播了廣府壁畫的文物價值,提高了廣東省對壁畫文物的重視,僅在廣州一地,就有番禺、黃埔、花都三個區陸續出版了自己的清代民國廣府壁畫圖錄。黃利平初到虎門炮臺管理所時,發現鴉片戰爭前的炮臺名稱被寫在了光緒時期所建的西式炮臺上,為此他專門發文《以訛傳訛何時了——說廣州所屬虎門炮臺的分期》進行了更正。 黃利平是廣東省唯一在縣級文博單位工作的研究館員,他深知基層文博從業者的艱辛忙碌同時還得不到社會廣泛認識和理解。然而,他覺得能一步一個腳印,不斷發現文化遺存,并在調查遺跡、整理資料和探求研究中,與歷史貼心對話,為他工作過的地方增添文脈色彩和文化積淀,是平凡中的光榮。他說:“這30年來我不斷挑戰自己,發現未知,力求創新,無愧于我熱愛的文博事業。”(張麗卉) |
相關閱讀: